很早以前,我母亲曾在舞台上是那么风光。
她是团里的名角,那个赫赫有名的小百花越剧团。有人说,她鬓角一画,眉毛一描,要比男人还俊俏。
剧目里的梁山伯要演位置一定是要留给她的。那身段,那姿容,“啪”一声抖开一把折扇,清朗地道的唱腔,在越剧迷们的心中,梁山伯的影子和她一分不差地重了。
我母亲那时正值青春,心高气傲,身边不乏追求者。谁也没有想到,她也会偷偷喜欢一个人。
我父亲拉得一手好越胡。名角的唱腔再婉转,再动人,也要好乐来衬。帷幕一拉开,我的母亲受万人瞩目,我的父亲则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拉着他祖辈传下来的越胡。
江浙之地乡下有很多土庙,庙里供着些散神,香火一般冷清,只有到农历的九月才会热闹一回。九月稻子第二回熟,哪怕今年收成不好,哪怕再穷,村长也会遍请乡绅,募集好钱,请来最好的越剧团,让村民饱一饱耳福。
土庙里搭建的戏台,一年特地为越剧团空出360天。
没人知道我母亲心里悄悄住下了一个人。她爱得很小心,爱得很克制。舞台上水袖翻飞,眸光流转,她也只敢在转身的时候悄悄向那个角落里瞄上一眼。
父亲在拉越胡。他拉得是那么忘情,以至于他似乎忘了他仅仅是给别人伴奏而已,他似乎成了舞台的中心。
曲终落幕,台下掌声雷动。父亲一惊神,才发现此刻没有一双手是为他鼓掌的。他看向台上,看着母亲清癯的背影,消失在了红帷之中。
越剧团里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一年之后,他们在一起了。
有人说,是我妈倒追我爸的。我母亲用了一个晚上写了一封信,寄上自己的一绺青丝。上面写道:
“侬十五一个人来五龙桥找我。记着哦,侬一个人。带上越胡,只许弹给我和月亮听。弹一首《梁祝》,偶就算从了。”

(二)
我母亲很心疼她的丈夫,两个人结婚有两年了,我母亲在我父亲面前还是羞答答像个小姑娘。台上母亲风情万种,受人追捧,一回到家中就如同无数凡尘中的女子一样,心甘情愿地灰头土脸,洗衣,做饭,默默为这个家付出。
我父亲在家里连碗都没有碰过。很多人都纳闷,我母亲到底是怎么看上我爸的。我爸出身也很一般,祖上三代都拉越胡,家境也不优渥。
有人猜测,是越剧团里清一色女流,我父亲作为少数的男性,模样长得还可以,情深日久,真白白便宜了这个小白脸。
父亲有时候闲下来对着阳台拉一首小曲,母亲贴着门,一只手提着水桶,一只手攥着抹布,弓着沉甸甸的背,用的却是台上的莲步,蹑手蹑脚地贴着墙从客厅穿过,生怕打扰他一分。父亲一转头,母亲急忙倏忽闪到门的后面,像个十六岁豆蔻初开的小姑娘。桶里的脏水溅了一地。
父亲的越胡拉得如此好吗?拉得能把一个女人的心吊住。说实话,我觉得我父亲的越胡拉得很一般。越剧团里拉越胡的有三把手,我父亲连其中一把手都不是。我祖父的越胡拉得是真好,拉到能喧宾夺主,拉到国家聘请外国友人观赏也一定要把我祖父请来。
民间技艺一派大抵都讲究顺个人情,我父亲自然就谋一个位置,成了替补的替补。
但世界上还是有两个人觉得我父亲的越胡拉得好。其中一位是他自己。
两人结婚后的第二个年头,我被母亲的身体“弃”出来了。为什么用一个“弃”字呢?我是她的累赘,在她黄金一样的年纪里耽误掉了半年的青春,半年母亲没有上台了。半年的时间太长了,够人心变一百次了。
我从来不觉得我母亲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她太平凡了,你看这熟练地擦桌子,熟练地洗衣服,熟练地将一把漆黑的越胡反复擦得锃亮。烟火里的女子完全是按照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直到我八岁那年,第一次看到母亲上台,我偷偷躲在帷幕后面,看见台下千百双眼睛,像探灯一样照过来,每一张脸上都是兴奋、激动、陶醉、享受。
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母亲和父亲吵过架。有的话只是十岁那年,不知道算不算的上。
我躲在门缝后面,听见父亲说,他不拉越胡了。他的语气很平淡,很自然,完全像是跟自己说的。我母亲赶忙问这怎么可以,你拉得明明很好。
我父亲猛把越胡摔在地上,“我窝囊了半辈子,才他妈晓得自己拉了二十年的狗屁!”
母亲不说话,只是把地上的越胡捡起来,放回原来的位置。
(三)
父亲说他去做生意了。跟几个朋友说好,拼钱办个小厂子,做个小老板。南方弃诸业从商的人很多,母亲没有说话,父亲就当她是同意了;母亲知道父亲当她是同意了,自己便对自己同意了。
我只知道,这半年来,父亲没了稳定的工作,家里的营生,都是靠着母亲那一份月钱接济着。偏偏这半年生意还不好,农村里老一代的人少了,年轻一代听不懂越剧,土庙的香火愈发衰微,渐渐地和草一并荒了。
父亲出去做生意之后,没向家里打过半分钱。我害怕极了家里的座机,只要一响,母亲就像第一次收到情书那样,郑重又矜持,惊喜又胆怯地接电话。
父亲和母亲的谈话从不超过一分钟。父亲挂断电话后,母亲守在座机旁,可以默好久。
“他是不是又找你来要钱了?!”我气急败坏地对着母亲喊道,“你自己过去在台上那么鲜亮,现在连给我买条小裙子都舍不得!我同学都有好看的新裙子穿,我也要。”
父亲名不见经传的厂子像个巨大的虹吸装置,透支着家里的存折,透支着我的母亲。家里莫名其妙地多了一个节日,就是父亲做生意回来的那一天,母亲像过年一样,把家里角角落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父亲回来穿着西装,脚踩着一双温州皮鞋,抽烟、喝酒,完全不像以前那个父亲了。母亲初次见到父亲时盯了好久,想要瞧出什么熟悉的东西来。但是父亲朝她看一眼,母亲又娇羞地把头低下去。
父亲头一次给家里带回来前。他把十摞钞票放在桌子上,一共十万元。母亲睬都没有睬一眼,她觉得父亲现在成熟的又成功的样子,似乎比过去多了一份迷人之处。

我爱我的父亲。
我父亲给我买好吃的。
我父亲带我去游乐园玩。
我父亲会给我买心爱的小裙子。
这些都是那个吝啬的母亲从来都不给我的。她的心思有十分,我就只能得到半分的半分。我以后要考大学,离开这座城市,找一个爱我的人。
父亲在餐厅里看着我吃冰淇淋,突然对我说道:
“你想不想要换个妈妈啊?”
我以为父亲这句是个玩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想。”
(四)
父亲求我一件事,让我对母亲说离婚这件事。他叮嘱我,千万别让母亲闹,否则人家看了要笑话。
我反问父亲为什么他不当面去问。
父亲说他知道自己亏欠了太多,有点,有点说不出口。
父亲说他们离婚是为了两个人的幸福。这点我是赞成的。试问这天下,哪有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让我感受不到一分爱,让我连“雨中送伞”,“医院陪伴”这样的套路作文都没素材写。
母亲为了一个人而形销骨立。要是心和肝不能挖出来,她巴不得把它们都送出去。
我一回到家,就没给母亲好脸色看,喊道:
“爸要和你离婚!”
“爸叫你不许闹!”
我以为她会哭,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或者哭得一枝梨花带春雨。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
我就看着母亲,躺在沙发上,身体软下来,像解脱了般长长呼出一口气。闭上眼睛。

(五)
母亲不唱戏之后,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戏服,手镯,头饰,都是剧团里的公产,她想要把它们卖了补贴家用都卖不了。倒是过去戏迷们打赏的首饰,母亲一件一件都拿去卖了。
现在我长大了,也懂事了。我在幼儿园里当老师。小孩子那个调皮呀,我每天都像鸡叫一样喊破喉咙。我渐渐体谅到了母亲的不易。我才晓得,原来我父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渣男。
“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渣男’,侬晓得伐?”
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我站在旁边,对她说道。
母亲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侬还爱伊否?”我又问。
母亲像应试教育的学生一样,摇摇头,忙答道:
“不爱了,不爱了。”
我母亲现在五十刚出头,还是半老徐娘风韵犹存,衣服穿起来比我还洋气。我一有空就带她出去逛街,我母亲渐渐变回了一个正常人,知道如何为自己而活,知道生活最后终究是属于自己的。
一回到家,我又不放心地偷偷问一句:
“侬真的不爱了?”
这次母亲想了好久,想了好久之后才答道:
“真的不爱了。”
“那行,我带侬相亲去!”
“啊?”
我想给母亲找个老伴,一是有人陪,互相照顾,作为子女能够省心;二是什么时候能拍张照片寄给那个人,那个人现在活得风流潇洒,我母亲活得也不差。
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了我的请求。
“不行的!不行的!都一把年纪了,侬不要脸,偶还是要点脸的!”
(六)
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又活了好几年。渐渐足不出户,记性也差了。后来诊断为奥兹海默症,连我都不认识了。
像这样的时代家里总会留传一件古董。我母亲的古董就是一个红木箱子,很大,比她要大很多。
天气好的时候,她会把红木箱子拿出来晒晒太阳,像推棺材盖一样,把里头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日暮的时候再一件一件放回去。
她每天都如此。
这件事我是听她邻居的说的,我母亲现在一直把我当贼看,她一见到我,就“哇哇”地大哭。
尤其是那个红木箱子,我真是摸都摸不得。我稍稍看一眼,一个小老太就拿起一个小木棍,用视死如归的眼神瞪着我,我只好苦笑不得地悻悻而去,走之前为她洗个衣服,或者热点菜。
零几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母亲的葬礼。
后来,我怀着好奇打开了我母亲留下的红木箱子。
里面孤零零地只躺着一把断弦的越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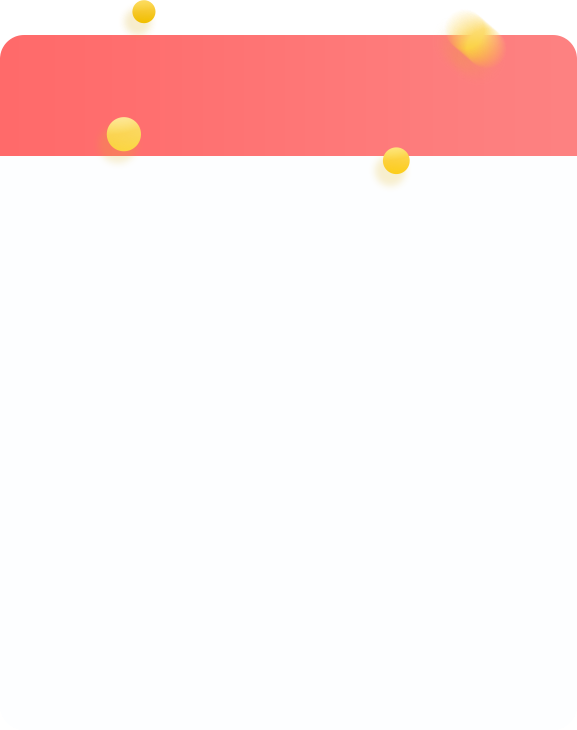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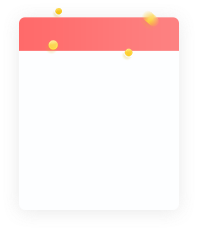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