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爱上了一个女孩,女孩和他在同一幢写字楼里上班,在同一个食堂吃午餐。
两人在大堂里、电梯里、食堂里经常碰到,闲聊了几个月后,女孩终于答应下周和他共进晚餐。
刘铮心花怒放,知道女孩喜欢优雅的餐厅,于是翻看大众点评网,又忙不迭请教同学,删选出一家符合女孩偏好的西餐厅。为了确保无虞,他还提前实地赶去了那家餐厅,试吃了一次。感觉环境、菜品和服务都很不错,才约上女孩。临去餐厅前,他把车里里外外擦洗得干干净净,备好女孩喜欢喝的饮料,和女孩喜欢听的CD,还给副驾驶座添置了靠枕和颈枕,贴心到每一个细节。
那天,在精心选择和布置的环境下,他和女孩相处得很愉快,两人开始进一步交往。女孩喜欢看村上春树的小说,为了和女孩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刘铮把村上春树的全套作品买来,一本一本啃。女孩喜欢听音乐,刘铮下载了所有女孩喜欢的曲子,一有空就听。看到女孩喜欢的演奏会,无论多么热门,都要想尽办法买上票,邀请女孩一起去观看。

女孩练习书法多年,刘铮搜集了很多书法帖子,到碑林之类的景点旅行,也不忘花高价给女孩带上一份拓片。
虽然刘铮自身并不喜欢这些,可是出于对女孩的爱,他都甘之如饴地做着。
女孩住城市东边,刘铮住城市西边,他每天早晚都绕大半个城市,接送女孩上下班。除了出差,风雨无阻。那情形,就像电影《真爱至上》中那句台词,“一天中我最愉快的时刻,就是送你回家。”心里有爱,做什么都浪漫。他把女孩宠上了天,丝毫不感到疲倦,反而有种浓浓的幸福感。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卑微的开始表现,就是迁就。
02
两个月后,女孩爱上了另一个男孩,慢慢开始疏远他,也不回他的微信。
刘铮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每次舔着脸找她聊天,结果几天都没回音。
忍不住厚着脸皮打电话,女孩草草敷衍两句,说:“我很忙,有空打给你,就挂了。”
她的冷淡,让刘铮的心空落落的,心痛到窒息。
他怕女孩反感,不敢轻易再打电话,只能时刻隐匿在黑暗里,偷偷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
女孩随口一句无心的承诺,他却眼巴巴地苦苦守侯。可是两个礼拜过去了,女孩依然没有打电话给他。
刘铮满心的期待转为失望,就像从高空狠狠坠落下来。他按捺不住,鼓起勇气又去找女孩。
这次女孩直接说:“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刘铮的世界在那一刻瞬间崩塌了。
他已经习惯了围着女孩转,不知道没有女孩的日子,自己该怎么活下去。
他努力挤出一丝微笑,问女孩:“我有什么做错的地方吗?告诉我,我改。”
女孩突然很烦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爽快啊,我们又没确定恋爱关系,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可是刘铮舍不得,还是想和女孩在一起。他越心急,就表现得越糟糕。
他天天等女孩上下班,但女孩看到他就绕道走,不愿意再坐他的车。

很快,女孩的男朋友开车来接送她上下班了。看着女孩和他亲昵的样子,刘铮感觉自己的心在滴血,那一刻,恨不能冲上前去砸了那辆车。
晚上,他恼羞成怒,疯狂地开车来到了女孩楼下,发微信让女孩下来说清楚。
女孩说:“没必要,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随后拉黑了他的微信和电话。
那晚,刘铮在车里像头困兽,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把自己的肺都要熏黑了。
烟抽完了,他泪流满面,趴在方向盘上哭成了狗。
直到早上,小区里的人开始陆陆续续出门上班了。他知道自己纠缠不清的样子很难看,不想女孩出来看到自己这副没志气的样子,才发动车子缓缓离开。
冯唐在《万物生长》中说过,“一个人经过一个女友就像一个国家经过一个朝代,好像清干净了,但是角落里的以及脑子里的印记会时常冒出来,淋漓不净。”
几年后,刘铮偶尔想起那个晚上,依然能感觉到那种锥心的痛。
03
刘铮浑身的精气神都被抽空了,请了一天假,回家倒头就睡。可是脑袋就像炸开了似的,怎么也睡不着。
次日清晨,强打起精神去上班。可是身体不听使唤,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好让自己不会随时倒下。
那是他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他爱她,却无法联系她。
世上最难断的,大概就是感情,明知不可能,还是令人不能自拔。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日日夜夜的折磨。衣带渐宽终不悔,分分秒秒的牵挂。
刘铮整夜整夜地睡不着,陷入自我评价极低的状态里,情感和理智不断拉扯,难分胜负。
他知道自己应该潇洒地挥挥手,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可是,内心却依然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迎合女孩,全心全意想要表现好一点、更好一点,只要女孩不离开她。
可是不爱你的人,说什么都没用。那个打定主意要离开你的人,再怎么抢天呼地也留不住。你的卑微只会让她更看不起你,更加不懂得珍惜你。

谁说过,离开一个人的时间,大约是恋爱时间的二倍。刘铮沉迷于失恋的伤痛中,整整3个多月。
第99天,他清晨醒来,看到窗外的微光从窗帘的缝隙透进来,突然感觉胸口不再那般疼痛了。
他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轻松和喜悦,觉得该让过去过去了。
不被爱只是不走运,而不会爱始终不幸。越是没人爱,就越是要爱自己。
04
若干年后,刘铮和女孩已各自成家。
当他在街头和女孩再次相遇,竟觉得非常陌生。
他感觉难以置信,当初怎么会对她如此迷恋,在她面前那么低眉顺眼,那么不由自主地恐慌和软弱。
那种感觉,就像尼采研究叔本华时的独白,“我自问,在他那么不爱的世界里,我怎么能够表现出那么多的爱?”
我们都曾在某个时间段,为了某一个人,忘乎所以,失去理智,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我们以卑微的姿态,在那场关系里存活,认为对方远比自己更重要,拼命去适应对方,以至于放弃自我。
其实对方一直就是那个样子,是我们自己,助长了那份不平等的情感契约。
时过境迁,才慢慢发现,其实那并不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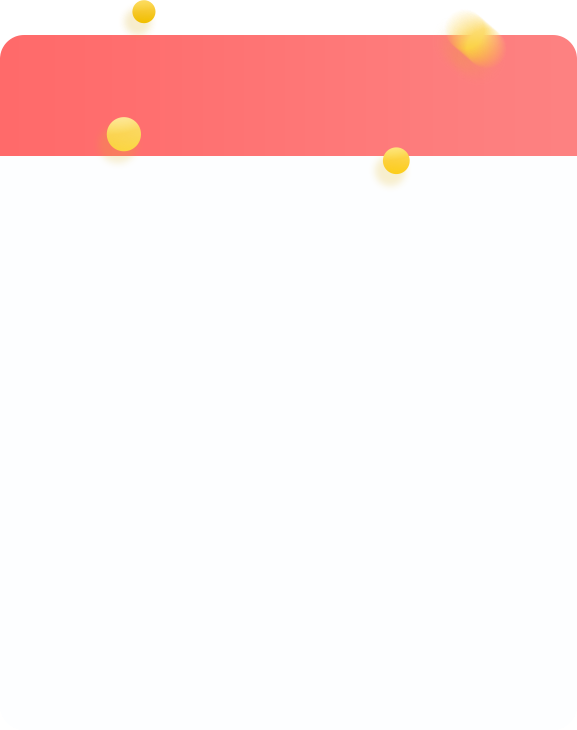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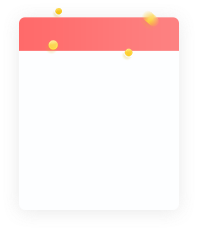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