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一个寻常凌晨,一位名叫陈平的女作家在医院自缢身亡,她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三毛。 这年,她才48岁。
她毫不留恋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得知消息那天,摄影师肖全,推着自行车,与妻子走在冷冽的成都街头,他说:“要是我今天能在外省就好了,我就可以去参加三毛的葬礼。”
与他同行的妻子回应:“三毛只有生日,没有葬礼。”

对于很多当代人而言,三毛的名字意味着遥不可及的远方沙漠,以及,爱情。
很多人误解了,三毛也是一位普通女性,她短暂的人生,不是可以简单被“浪漫”或是“流浪”二字囊括的。
她遭受过身体的各种病痛,爱人的生死别离。不必将她的经历过度浪漫化、传奇化。
滚滚红尘,三毛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01
“想到二十岁是那么的遥远,我猜我是活不到穿丝袜的年纪就要死了,那么漫长的等待,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
一条丝袜,在三毛读中学时期,就成为某种预言。
1943年春天,三毛出生于重庆南岸区黄桷垭正街145号,知识分子父亲陈嗣庆爱国心切,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便给二女儿起名为陈懋(mao)平。
“懋”字是家谱上的排行,对此三毛表示抗议,只因这个字过于难写,她自作主张将这个字去掉,改名为陈平。
父亲没有办法,不得不把她两个弟弟名字中的“懋”字也一同去掉。
在父亲陈嗣庆眼中,女儿自小就显示出某些不同,三毛小时候最喜欢在过年时,观看大人杀羊,看完后脸上还会露出满意的神情。

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女儿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948年,三毛随父母离开故乡重庆,移居外省。
她从小就喜欢读书,最爱不释手的是《红楼梦》,在童年时期,三毛就了然到其中苦痛。
当她念到贾宝玉失踪,贾政泊舟在客地,当时,天下着茫茫的大雪,他一抬头,看见一人双手合十,面部似悲似喜,那人正是宝玉。这时候突然上来了一僧一道,挟着宝玉高歌而去。
当三毛看完这一段时,抬起头来,忘了身在何处,她只是坐着出神,顿悟到“境界”二字。
她称那是自己一生一世都要看下去的书。
“每天清晨,我总不想起床,被母亲喊醒的时候,发觉又得面对同样的另一天,心里想的就是但愿自己死去。”
个性十足的三毛,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噩梦就此降临。
她不合群,不玩任何女孩子爱玩的洋娃娃、跳绳等游戏,三毛常常一个人去荒坟玩,同学们都离得远远的,她才不怕。
上小学时,老师让大家写作文《我的梦想》,三毛写下的梦想是当拾荒者。
老师让她在课堂上朗读自己的作文,她说:
“我有一天长大了,希望做一个拾破烂的人,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还可以大街小巷游走玩耍,一面工作一面游戏,自由快乐得如同天上的飞鸟……”
这个奇特的梦想,让她挨到了老师的批评,三毛被迫将自己的梦想改成了卖红薯的小商贩,老师仍然不满意,最后她默默地写下了医生,嘴角却露出苦涩的神情。
也许那时的三毛,就在将流浪寄托于拾荒者的梦想上。

02
12岁那年,三毛考上了外省第一女子中学。
这所学校名声很好,可是在这里,她丢失掉了一个孩子的尊严。
读初二时,向来数学成绩不好的三毛在一次考试中获得了满分,老师认定她作弊了,直接拿起毛笔蘸着墨水,在三毛眼睛周边画了两个大圆圈,还让她在校园里走了一圈。
同学们讥笑不已,内心敏感的三毛怎会受得了这等屈辱,她开始逃学、自闭、甚至想到自杀。
之后,她被诊断为自闭症。
三毛开始了漫长的休学时光,她让父亲给自己房间的门窗都上了锁,白天也要拉上窗帘,仿佛只有这样才是安全的。
姐姐与两个弟弟每天去学校正常上学,人乖顺,成绩也不错,每当三毛听到他们回到家讨论学校的事情,她就捂着耳朵躲回房间。
三毛最害怕的时刻,是父亲每天下班回到家后,在自己门前的那声叹息,她也想做个快乐的孩子,可是她做不到。
“父亲一生没有打过我,但是他的忍耐,就仿佛在告诉我——你是一个让父亲伤心透顶的孩子,你是有罪的。”
休学的三毛,在家里由父母教育,父亲让她看唐诗宋词,看《古文观止》,读各种英文小说。
除了在家读书,她最常去的地方是家附近的公墓,她觉得和死人作伴很安全。
在医生的建议下,父母将三毛送去学习钢琴与国画,三毛对绘画老师顾福生说:
“我不是一个能够苦练下功夫的人,如果我能苦练,也许在绘画上会有点小成就。”
这年,她16岁。
事实证明 ,三毛在绘画上没有天赋,可老师顾福生发现自己的这个学生,在文学上很有灵气,便将她的作品举荐给了《现代文学》的主编白先勇。
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从年少时期三毛就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身体也总是病症不断。
这种敏感、细腻的特质,成为一种天赋,让她在文学创作上,显示出别样的生命力与才华。
那年,三毛的第一篇文章《惑》被发表在《现代文学》期刊上。
在这部处女作中,她不断重复一句话:“我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
这部叫作《惑》的处女作,像是一棵救命稻草,将自闭的三毛从深渊中拉了出来。

03
在文学世界中寻到认同感的她,重新拾回生活的信心,开始不停地写文章,也接触到了哲学。
1964年,三毛到刚刚创立的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做旁听生,同样在此就读的蒋勋常常看见三毛走在校园,唱歌、大笑或者独自沉思。
那是个纯真的年代,那时候学生们不热衷于考试,不热衷于学位,中国文化大学只有两三届学生,大家彼此都认识。
蒋勋常去哲学系上课,比三毛上的课还多,当时的三毛追求戏剧系一位男诗人,有时她扎着长长的麻花辫,在校园草地跳舞,有时她散着长发忧郁独行。
三毛忙着写作,忙着谈恋爱。
她对戏剧系的那位男诗人爱得死心塌地,可是对方并不动情,三毛终于在追寻了两年后失恋,这场苦涩的初恋,让她很受伤。
最终,三毛决定离开外省,远赴西班牙疗伤。
1967年,她来到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就读,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三毛遇到了给自己之后人生带来无数惊喜与战栗时刻的男人——荷西。
彼时的荷西还是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对三毛一见钟情,大胆表白:
“Echo,你等我六年,我还有四年大学要读,两年兵役要服,等这六年一过,我就娶你。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公寓,我出去赚钱,回来之后,你在家里给我煮饭吃,这就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了。”
大荷西8岁的三毛觉得面前这个男孩很幼稚,也怕他纠缠自己,便说:“好啊,不过6年时间太长,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从此你不要来找我。”
两人就此道别。
三毛继续恋爱、失恋、读书,她在人潮中寻觅着属于自己的爱情,可每段感情都让她失落。
1970年,三毛回到外省,被邀聘到中国文化大学德文系、哲学系任教。在这里,她与一位德国老师相爱,没多久两人就准备结婚,可就在结婚前夜,未婚夫心脏病突发,最后死在三毛的怀里。
三毛感觉天要塌了,她默默吃下一瓶安眠药想要自杀,还好父母及时发现将她送往医院。醒来后,她决定再次出走。
1972年,三毛重返西班牙,在朋友家中与荷西重逢。
三毛知道那是命中注定的爱人,她与荷西结婚了,也从马德里去到撒哈拉沙漠开启了一段异国婚姻生活。
荷西与三毛
04
三毛看见了一张撒哈拉沙漠的照片,感应到前世的乡愁,于是决定搬去生活,苦恋她的荷西也二话不说跟着她去了。
三毛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片陌生的沙漠。
沙漠里条件艰苦,没有房子没有车,甚至喝水也很困难,落日将沙漠染成血红色。
1974年,三毛与荷西在沙漠小镇阿尤恩进行了简单又富有的婚礼。
那年,她31岁,他23岁。
三毛与荷西 结婚登记
荷西送了一个完整的骆驼头骨给妻子作为新婚礼物,三毛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

他们在沙漠中的家,对面是一大片垃圾场,再前方是一片波浪似的沙谷,再远就是广大的天空。邻居们的屋子里看不到一个人,只有不断的风剧烈地吹拂着三毛的头发和长裙。
荷西将三毛从背后抱起来,他说:“我们的第一个家,我抱你进去,从今以后你是我的太太了。”
三毛与荷西
三毛知道这是一种平淡深远的结合,她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热烈地爱过他。
在撒哈拉沙漠,三毛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日子,她也将自己的沙漠生活写成书,《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温柔的夜》相继问世。
她用细腻的文字,将大漠的狂野与温暖的婚姻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三毛热”迅速地从外省横扫整个话语文学圈,“流浪文学”从此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不过,家人从不看她写的书,只是用来送礼。
三毛觉得自己在家庭中,是备受冷落的,父亲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觉得女儿总是将家庭与乡愁,作为情绪的出口。
每次三毛寄信到家里,总要求父母也要讲家中的故事回应她,如果字数太少,她会很难过。
1976年,因撒哈拉Z形势变化,三毛与荷西搬到了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她继续写作,他找到了一份潜水员的工作。
命运造弄,安定的归属突然消失。
荷西与三毛
1979年,荷西在执行潜水工作时溺水身亡,三毛悲痛欲绝。
她看着失去生命体征的爱人,没有哭泣,只是紧紧拉着荷西的手,念叨着:
“你要经过一个黑黑的隧道,你不要怕,我握着你的手,你勇敢地走过去,虽然我不在你身边,过了隧道,那边有神会来接你。现在我有父母我不能跟你一起走,过几年我再来赴你的约会。”
荷西与三毛

05
三毛的灵魂仿佛被带走了,在荷西葬礼结束后的那几个小时,她被打了镇静剂躺在床上,药性没有作用,她仍然在喊:“荷西回来,荷西回来!”
远在外省的父母担心女儿,远渡重洋到这里来看望。
父亲陈嗣庆站在一旁,近乎崩溃,母亲缪进兰强行保持镇静,发着抖在厨房用一个小平底锅炒蛋炒饭,给女儿的婆婆与荷西的哥哥姐姐们做饭。
以后的日子,三毛不知该如何度过,她时常想起那片与爱人共同生活过的异乡:
“那片墓园曾经是荷西与我常常经过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厌地怅望着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寂寂的土地,好似乡愁般地依恋着它。”
她的爱,浓烈而执着。
荷西去世后,三毛在父母的扶持下回到外省,就此结束自己长达14年的流浪生活。
她的精神世界,正在坍塌,也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三毛收到了《联合报》的邀约,赞助她在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她回到外省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进行了环岛演讲,非常成功。
“我的文章将就是我的生活,我写的其实只是一个女人的自传。”
1981年秋天,外省高雄文化中心热闹非凡,偌大的至德堂单曲循环放着齐豫的《橄榄树》,这首歌的作词者是三毛,“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
大家在此等待三毛女士。
这是她回外省后的一场演讲,三毛的声音温柔动听,演讲结束后,她说了句:“三毛不值得你们这么爱,回去吧,做更重要的事情去。”
父母心疼女儿,日日夜夜伏案写作、奔波演讲,他们总以为三毛回家了,结束流浪生涯,离开那个充满悲苦记忆的小岛,可以快乐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说自己的语言,开始她的新生。
但是回到外省后的三毛常常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大小疾病频发,她还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她讲授的“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备受学生喜爱。
母亲缪进兰说:“日子无休止地过下去,不知哪一天这种忙碌才会停止。社会太爱她了,而我们实在受不了。”
每次当三毛从一场讲座、一个饭局里走出来,她的脸上虽然挂着笑意,孤独却是彻骨,任自己恍惚沉溺,甚至会忘记回父母家的路。
荷西死后的这十几年,三毛一直活在挣扎与痛苦中,关于生死的命题她总在思考。
好友们很关心三毛,想要平抚她内心的创伤。
荷西去世后,琼瑶给三毛打去7个小时的越洋电话,直到三毛答应她绝不自杀。
1990年,肖全在成都给三毛拍了那套著名的照片。

肖全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三毛时的场景,彼时47岁的她穿着一件白色衬衣,盘着头发,在抽烟,讲起话来非常利落。
在正式拍摄时,三毛换上了乞丐服,散下长发,肖全觉得很有趣,他对面前这个有灵气的女子说:“我发誓能给你拍出好照片来。”
后来的摄影作品,验证了他的这句豪言壮语。
肖全为她拍的那些照片,被公认为是最接近三毛精神内涵的作品,她的眼睛里写满哀伤,谁也走不进去。
肖全所理解的三毛的精神是:敢生、敢死、敢爱。
三毛低头不看任何人,她害怕自己被人群堵住,更怕听到三毛这个名字,她总觉得这人间悲凉。
她瘦削而孤绝,衣着还是像在撒哈拉沙漠,有一种不合时宜的荒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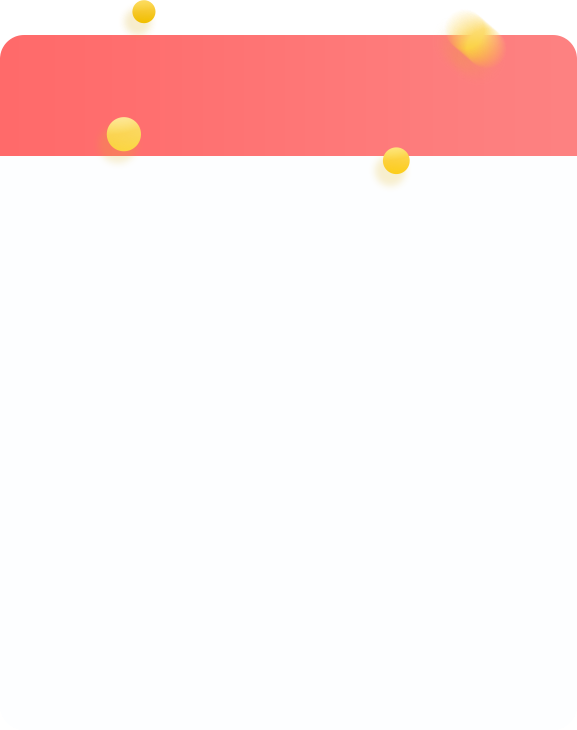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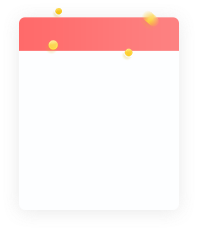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