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的女人洗完衣物后又开始扛起锄头外出了,地里,和他儿时同样顽皮的孩子正手执细小枝条驱赶地里翩翩飞舞的菜粉蝶。女人朝孩童嘱咐了一声,后者却只顾着头顶的热闹不小心在地里摔了一跤,鼻尖上磕着泥巴。女人扔下锄头,迈着极为不优雅的步子跑到孩子的身边生气地将他弱小的身体提起,大声责骂,大掌将他的身子翻来覆去,眼睛像是猎犬一般不肯放过任何一条细微的伤口。中午吃饭,女人在他面前又将孩子数落了一顿,他只是嗔怪女人太小题大作,在这世间摸爬滚打的人,谁没得个磕磕绊绊的,女人气鼓鼓地不再说话,他拍了拍宝贝儿子的头叫其多吃点好快点长高,儿子眨巴着眼扒饭的速度更殷勤了。他点头心里直赞许――孺子可教,而后将剥好的花生扔进嘴里。
电视机里放映着各色的男男女女,他的女人看的津津有味,男人却对其并不敢兴趣,可那个跟他吃苦的婆娘唯独这点爱好,他不好剥夺。

夜幕降临,女人在屋里烧饭,孩子在门口蹲着玩他心爱的塑料火车,家里的土狗似乎对这儿童的游戏很感兴趣,在儿子身边使劲地摇晃尾巴,而一家之主的他终于在一天忙碌后放松地坐在院坝里抽了杆烟。
微风吹皱了幽深的湖水,涟漪一层一层排开,颤动了夜幕之上亿万的繁星。男人朝天空吐了一个烟圈,又叫风搅散,往往复复,清风狂放,竟一点也不怕惹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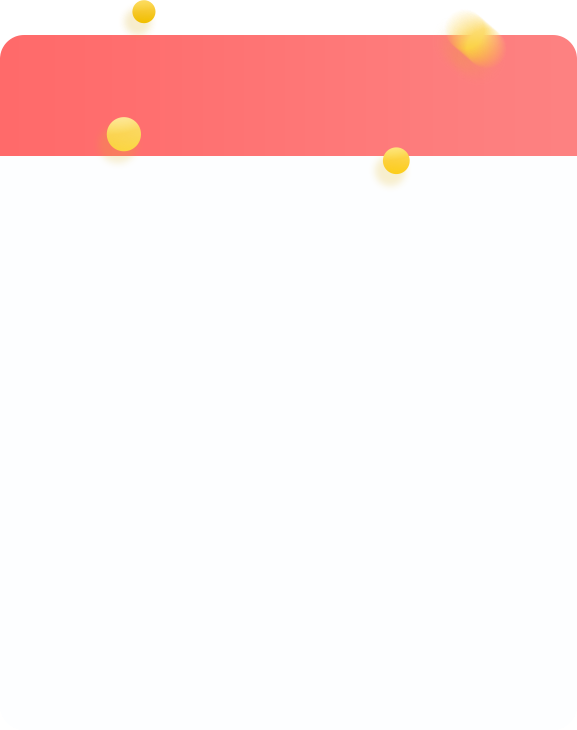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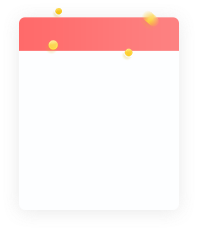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