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罗师傅处理完后厨里的突发事故,急匆匆赶回家里,见到的却不是自己临时叫来看孩子的徒弟小张。而是来找孩子的杨老师,正坐在满地狼藉间抱着蓓蓓痛哭。见罗师傅回来,向来文弱的杨老师扑过来就是一耳光,把罗师傅打得有点懵。“看看你徒弟小张干的好事!”杨老师哭得声嘶力竭,手里拎着条染血的小内裤,“那个畜生!我们蓓蓓才四岁!他怎么下得去手!”罗师傅猛然僵住,目光越过还在哭喊的杨老师,看向坐在地板上的小女儿。蓓蓓乖乖巧巧地坐在那儿,两条光生生的小腿随意摆动着,漂亮的小脸蛋上蒙着一层懵懂,并不明白自己刚才究竟遭遇了什么。她看见罗师傅回来了,立刻笑了起来,朝罗师傅伸出手:“爸爸,我饿了,我要吃蛋炒饭。”罗师傅耳边轰的一声响,什么都听不见了。他几步跨过客厅进了厨房,看见案板边还摆着那把杀鱼刀,刀刃锋利,寒光瑟瑟。
罗师傅记不清自己这辈子究竟用那把刀宰杀了多少鸡鸭鱼。但用来捅人,单单就只那么一回。人的骨肉并不比寻常的鸡鸭鱼更为坚韧,更何况罗师傅的刀工本来就是出奇的好,一出手便能避开关节筋骨,直直往要害里扎,血花瞬间迸了出来,喷了罗师傅满脸,还带着温热。被扎的小张靠墙缓缓坐了下去,嘴巴剧烈开合,像条被剖开的鱼,徒劳挣扎。但死鱼的眼珠总是木讷黯淡的,小张的眼色却还透着疯狂与凶恶。他半笑不笑地盯着罗师傅,脸色白惨惨的:“师父,你以前只管出气骂够了我,眼下我也毁了你女儿,咳咳,我……我不亏了……”刀“哐当”一下从罗师傅手上掉下来。一贯暴脾气的罗师傅手足无措地跪倒在地上,嘴巴张了又张,却说不出一句话。

后来杨老师去探监,罗师傅交给她一张签好名字的离婚协议书。“钱都在存折上,房子你卖了,带蓓蓓走,别再来看我了。”罗师傅说这话时,一点儿坏脾气都没有,语气挺和缓的。“是我对不起蓓蓓,就当她没有过我这个爸爸。”
等罗师傅出来,快二十年过去了。年富力强的罗师傅变成了满头白发的罗老头,没家人,没朋友,没财产,没工作。曾经存在于罗老头生活里的那些旧物事,就跟这城里被拆迁的老片区一样,早变了样貌,什么都没剩下。罗老头费劲巴拉地研究了好一阵子该怎么用智能手机,终于学会了该怎么在上面买去另一个城市的高铁票。一切都让他感觉很陌生。他不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不认识他了。
杨老师开门时,看到罗老头站在门外,稍微愣了愣神。倒不是惊讶罗老头要来,对方来之前给她打过电话的,只是面前这个干巴巴的老头跟自己印象里的罗师傅差别确实大,稍微有些不习惯。不过,曾经年轻漂亮的杨老师也老了,当年她独自带着女儿来到这个城市辗转安定下来,重新成了家,养大了孩子,如今自己也是快要退休的年纪。岁月不饶人,谁都不饶啊。杨老师客客气气地将罗老头请进屋坐下,还给他倒了一杯茶。罗老头接过杯子,环顾四周,看这家里倒是敞敞亮亮的,墙上还挂着一家三口的合影,低头喝了口茶:“蓓蓓不在家吧?”“对,今天单位正好轮到她值班,要晚上才能回来。”“那你家那位……哦,刘医生也不在?”“他去外地指导做手术了。”“蓓蓓她这些年都还好吧?”“蓓蓓挺好的,当年她还年纪小不记事,又换了环境,谢天谢地没受什么坏影响,调整得不错,早就走出来了,这些年都过的挺好。”罗老头双手抱着杯子连忙点头:“那就好,那就好。”杨老师从沙发上站起身,拿了开水壶要给罗老头的茶杯添水,罗老头连忙摆摆手说不用,杨老师便又坐下了,气氛是生疏的沉默。
罗老头手指在杯子上摩来摩去,影子映在水里:“刘医生对蓓蓓也还行吧?你们怎么没给蓓蓓生个弟弟妹妹?”杨老师笑得有些勉强:“老刘没有生孩子的缘分,是真心把蓓蓓当成亲闺女来宠的,蓓蓓也一直把他当亲爸爸。”听了这话,罗老头不言语了,只坐在那儿盯着杯里的茶叶浮在水面上微微打转儿。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来:“我在外头还有事儿,先走了啊。”“你不等蓓蓓回来了?”“让蓓蓓见我干啥,好不容易才换了个新环境,别再让她想起以前那些糟心事,你别跟其他人说,就当我没来过。”罗老头说着就往门外走,头始终埋着看向地板。“孩子有个杀人犯的爹这种事……传出去多不好听。”
之后罗老头没有再和杨老师有过任何联系。但他没离开这座城市,横竖是在哪儿都没有根儿了,就在这里停下也没什么区别。罗老头没有别的本事,只有当年的好手艺还残留了些,开正经餐馆是不可能了,钱和精力都兜不住,他在城乡结合部租了间破房子,再找辆二手三轮车,简易灶台往车上一搭,在城里写字楼区附近的夕水巷里开了个专门卖炒饭的小摊子。

每天蹬着小三轮早出晚归,也就挣个生活费。但这贫苦生活没能把罗老头压垮,他脾气还是大,来这里吃饭的人都知道,哪里稍不如那掌勺的罗老头的意,可能就要挨他一顿训。可大家还是喜欢来,喜欢看罗老头拽拽的炒饭派头,吃那盘香喷喷的蛋炒饭。要是赶上罗老头心情好,往炒饭里免费多加一个蛋一根肠,有时还附赠一瓶凉茶可乐,这种机会也不是没有。
后来罗老头的蛋炒饭因为实在太好吃,传出了名,来排队的人多了,罗老头也不涨价,还是一份炒饭该卖多少是多少,只是脾气往上涨了,成天指挥排队的年轻人们拿这个小菜添那个例汤,吃完的碗碟筷子该往哪里放,不听话的就要受他一顿暴脾气的训。就好像这破落的露天街巷,也是他主管的厨房似的。
时至半夜,刚下过一场暴雨,巷子里其他摊子都收了,冷冷清清没什么人。只有罗老头的摊子还开着,黑暗之中孤零零点盏灯,几颗蛾子绕着那昏黄的光线绕啊绕。从巷子外面走进来两个年轻女孩,站在罗老头的摊子几米开外,悄悄嘀咕了几句“听说他脾气特别坏”、“可我就想尝尝这个蛋炒饭”、“好吧,你挨骂了我可不管啊”之类的话,才心虚地往摊子前面站。“老板,一份蛋炒饭。”扎马尾的姑娘小声道,顺势望了一眼身边的同伴。“我俩分着吃,可以吧?”说完她立马往后退了半步,笑得很露怯。她早听说过这个摊子老板脾气特别臭,而且从来不单炒,自己和朋友怕不是正好撞枪口上。但预料中的暴脾气并没有来。掌勺的罗老头只轻声应了句:“小菜在那边,自己添,汤凉了不要喝了。”然后他就开了灶火,伸手在锅上晃一下试试温度,待锅烧烫。两个女孩坐在一旁的矮板凳上,看罗老头先是一勺子亮油锅中烧热,旁边筐子里捞出鸡蛋往铁锅沿上一嗑一甩,只听“滋拉”一声,鸡蛋便落在热油里,冒出青烟,烫起白泡。
罗老头手中的大铁勺捣在锅里,“哐哐”几下便把蛋清蛋黄打散拌匀,激起喷香。趁着蛋花将结未老,再一碗白饭从天而降,直接扣进锅里。罗老头挥着勺子在锅中熟练地打圈儿,又是一阵叮叮哐哐,米粒就都散了,跟蛋液混在一起,白粒浸黄。此时炉火更旺,罗老头一手持锅,一手把勺,就这么翻炒起来。米饭与锅底短兵相接,“卡兹卡兹”蹦得热闹,底下又有炉火呼呼作响,热浪香味扑了遍地。待饭炒好装盘,蛋炒饭里见不着蛋,炒出来的饭粒儿却是颗颗金亮,扑满蛋香。这是罗老头最拿手的蛋炒饭,练了很多年。

两个女孩坐在那儿托着盘子,你一口我一口吃得很香。罗老头关了火,就坐边上看着,听两个女孩轻松愉快地聊着些琐碎,关于工作,关于恋爱。还有扎马尾的女孩小小地抱怨了明明自己今天过生日,却要在单位加班忙到半夜以至于没空庆祝这件小事。“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过生日,我别的也不想吃,就特别想吃蛋炒饭。”“哈?你要求还真低啊,过生日随便一盘蛋炒饭就打发了。”“喂喂,好吃的蛋炒饭也是很难遇到的好不好!这家真是我遇到的最好吃的,这次生日过的值啊,哈哈。”女孩嘴巴里塞了一大口饭,吃的很满足的模样,然后她像是突然想起来了什么,偷偷靠近朋友的耳边。“之前不是都说这家老板脾气特别差吗?我看还好啊。”另一个女孩也觉得纳闷,两个女孩抬头望向罗老头之前站着的地方,却没见着他人影。
此时的罗老头正躲在边上一堵墙后面,任谁路过也看不出这个干瘪的老人家就是个那个骄傲又坏脾气的罗老头,因为他正卑微地弓着身子靠着墙,浑身不停颤,浑浊眼泪从捂着眼睛的指缝间漏了出来。只为女孩夸了一句他做的蛋炒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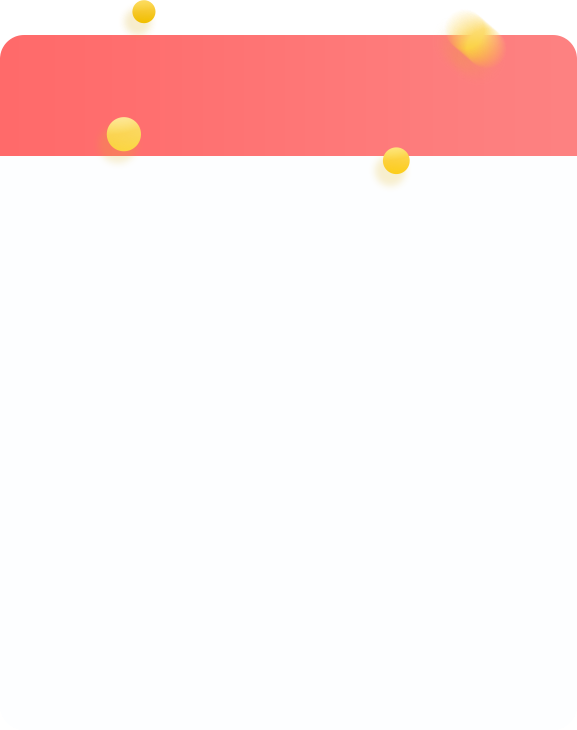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非微信浏览可先长按或截屏保存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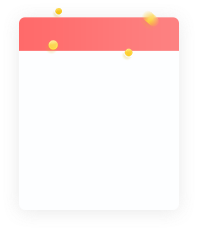 易倾咨询服务号
易倾咨询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微信识别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